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
2026年01月17日 星期六 距离高考:141天

“我的家乡有一条小河,有一条小河,从我家的门前静静地流过,静静地流过,每当我披着夜色来到河边,来到河边,她为我洗尘又轻轻的嘱托,轻轻的嘱托……”这首《家乡的小河》,是我上高中时,中午从录音机中收听的每周一歌,那男中音浑厚、低沉、深情、磁性的歌声令我们痴迷陶醉,至今恍然如昨。无论异土他乡,无论何时何地,只要一听到或想起这首歌就心潮澎湃,感觉时光倒流,思念就回到了家乡,回到了童年,回到了小河边……
我的家乡是冀中平原上的栾城,千年古郡,冀中形胜,其地貌大体呈西北高东南低走势,蜿蜒如带的洨河、冶河基本平行也自西北向东南越境而过,我们的村庄——西羊市位于栾城的北部,冶河(又叫运粮河)就从我们的村北穿过。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初,水量丰沛,村村有河,街街有河,条条小河,四季有水。我们刘家街的河不仅在全村最大,在附近十里八乡也是数一数二的。我家就住在刘家街的村西外,门前就是这条小河。每天出门从河边走,回家从河边过,在她的身边我走过了难忘的童年,走过了青涩的少年,走出了村庄,走向了外面的世界。我总觉得没有人能比我更熟悉热爱她了。
春天是小河最美的季节。小河的四周远远近近,高高低低都长满了树,尤其是南岸的那片柳林最为稠密茂盛。春暖花开,河水柔静纯蓝,河边芦苇丛簇嫩绿,翠柳鹅黄吐絮,杨柳依依,还有盛开的野桃花,槐树花,脆甜的榆钱……鸟儿在林中鸣唱,鱼儿在水中自由的游翔,小伙伴们在林中讲故事,捉迷藏,做中国打美国的游戏……扯枝柳条拧做口哨,学鸟叫,青蛙叫。村姑婶嫂在河边一边洗衣,一边嬉闹说着东长西短。打闹声,笑声,棰衣声,和着大自然的天籁之音,合奏出了一曲春天的交响乐。
夏天是小河最热闹的季节。无论是白天,还是晚上。天热了,到了酷暑,大人小孩都往河里钻。扎猛子,捉青蛙,逮蜻蜓,还有打香油的……最有趣的是吃过午饭,大人们(中青年男的)带着我们把离河边较近、水面较浅一角,用清泥截围成一圈,只在中间留上一个口子,然后大家开始合围着向里赶鱼,封口,然后都跳进圈内来回趟水,河水很快浑浊起来,不久变成了泥水,鱼儿呛的在水里呆不住了,拼命的浮到水面露出小嘴换气,大家便用鱼叉,筛子,笊篱、脸盆……叉的叉、兜的兜、捞的捞,抓的抓……闹翻了天,鱼儿真得不少,都是野生的,最大的草鱼至少也有三四斤吧,还有鲤鱼,鲢鱼,鲫鱼,泥鳅,野生的甲鱼(因为风俗上的忌讳,当时逮上了也只能扔回河里)……然后网兜着,柳条穿着,水盆端着,满载而归。
到了晚上,河水安静了,河岸、大坝上又热闹起来。夏夜里,这里是全村最凉快的地方。微风掠过水面吹到岸上,空气要比村里凉爽了许多,这里也就成了人们纳凉的好去处。月出东山,繁星点点,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。吃过晚饭,人们拿着软子(马扎)、小板凳来到河岸上,也有的脱掉鞋子往下一垫席地而坐,三五成群,说好话(讲故事)、闲聊天,历史掌故,风土人情,村里村外,天南地北,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”、“鲁智深倒拔垂柳”、“诸葛亮草船借箭”“黛玉葬花”“傻女婿见丈人”“狄家庄的驴落了实盘”老古话等等,无所不及。也有人喜欢讲鬼狐神仙的故事,有点故意吓唬我们,听得我们头发都竖起来了,往家走时紧紧抓着大人的手,不时的回头往后看,总觉得有个黑影在后面跟着似的。村里村外,十里八乡的新鲜事,稀罕事,在这里都有人说,都有人讲。孩子们最喜欢听二板叔讲的故事,他上过学,在石家庄钢厂当工人,晚上回来,他讲故事,慢条斯理,娓娓道来,“卓娅的故事”“流浪者”“五朵金花”“王成的故事”“董永的故事”,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些早期的中外电影故事。
秋天来了,河水变成了墨绿色,人们仍能听到鸟鸣蛙叫,鱼游虾戏。河水凉了,无人再下河了,可岸上晚上仍旧热闹,人们说着、笑着,感染的天上的星星一眨一闪,好像与人们同乐。记忆中的那时候,白天,蓝天白云,空气清新;晚上,皓月当空,星光灿烂。时间长了,故事不断重复,正当人们感到有些不新鲜时,县里有了电影放映队,轮着在各村放映。记得有一次晚上,人们正在河岸上哌搭腔,忽然有人说东头村(两村之间有座桥,西羊市叫西头,东羊市叫东头)演电影哩,大家信以为真,一哄而上,大人们在前面走,我和小伙伴们在后面跟着跑,那时村里自行车都很少,更甭说通信工具了,真是交通基本靠走,通讯基本靠吼,安全基本靠狗。我们连跑带走到了东羊市村,结果村里并没有演电影,这时有人说段干村演着哩,于是,大家不假思索的又往东去,段干村离我们村大约有十多华里的路,他们村在全县最早盖上了礼堂。在从西羊市到段干村的路旁,当时长着许多本地并不多见的一种树——绒树,可能是时间久了,它的枝干很粗壮,叶子像松柏一样翠绿,树上开的绒花就像粉红的绣球,煞是好看,可是,不知为什么大人们叫它鬼树、鬼花。传说许多鬼魂都隐藏在这树上、花中,谁只要一动到它,那野鬼、野魂就跟着潜伏到谁的家里,小孩们不知道爬了这种树,摘了这种花,家里人听说了,最轻的屁股上也得挨两脚。所以当地人都很忌讳这种树,尤其到了晚上更是害怕。尽管我们是跟着大人们,有许多人,心里也是很紧张的,好不容易到了段干村,到了大礼堂,一片黢黑,这里也没演这电影,这时又有人说八方村可能演着哩,这次大家都没有动,有人的脑袋开始清醒了,“咱们算一下,从段干到八方还有八里地,就是那里演着,等咱们赶到哪里,恐怕电影早已散了,咱还得往回走十几里地呢,不如趁早往回返吧。”于是,大家失望的只好往回走。走着走着,到了绒树旁,大人们出了馊主意,他们在前面突然一齐大喊,“有鬼,有鬼,赶快跑吧。”然后,撇下我们拼命的往回奔去,我们正在后面说小话,先是一愣,很快鬼哭狼嚎的追赶大人们,我们边跑边哭,摔倒了赶紧爬起来,哭着、喊着、骂着继续追,有的跑丢了鞋子,有的还被吓得尿了裤子……这个笑话在河坝上很是流传了一阵子。但是,不久小伙伴也把大人们涮了一把。又是去看电影回来,到了绒树旁,大人们故伎重演。他们喊完“有鬼”就拼命的往回跑,我们也装的鬼哭狼嚎的,就是原地不动,眼看着他们跑远了,我们便悄悄的钻进了路旁的庄稼地。大人们奔跑了一阵子,回头看不到我们的影子,便停下来等我们,一等二等不见踪影,他们开始有点着急了,有人说孩子们是不是晕向跑到别的他村了,他们开始焦急了,又有人说丢了一群孩子回去可怎么交代啊,老人们非砸断我们的狗腿不可。于是他们慌忙的返回来找人。他们一边小跑着,一边喊着我们的名字,一边互相埋怨着,我们趴在庄稼地里,一声不吭,眼看着他们向东跑远了,我们才钻出庄稼地向西返回到村里各自回家睡觉去了。大人们找了好几个村子也没见我们的影子,也不敢回家。一直折腾到后半夜,实在无奈,只好耷拉着脑袋披着露水回来了……这个笑话也在河坝上流传了一阵子。
冬天来了,河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,小河上又热闹起来。打皮牛、推铁圈、抛砖头、蹦琉琉、滑冰、打雪仗……我们在嬉闹中盼望着春的到来。
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,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最困难的时期,人们的温饱都不能解决,政治形势也非常严峻。当时还处在“文革”中,为了抓战备,还在这条河中间建了一条八九米高的大坝,晚上还在大坝上批判“地富反坏右分子”。他们当中有一个叫梁登山的人,他是黄埔军校第19期的毕业生,曾在冀州师范教过书,做过傅作义将军的副官,我的父亲很敬重他,私下里给我们讲了很多梁老的故事。他早年在外做官时,每次回村,一到村口就下马、下轿、下车,与乡亲们打招呼,嘘寒问暖。岁数大的他要鞠躬行礼,还送给礼物。他个子很高,很有风度,我们见到过他黄埔军校时的毕业照,一身戎装,帅气威风,平反以后到衡水做了政协主席。那时的批斗会,不光批,还打人,没头没脸的打,真有下手狠的。还有更绝的,为了证明已划清界限,让小子(儿子)带头批老子,不批不行,否则就是小反革命。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。附近村里有一个精明的小子,老子是反革命分子,他知道不批过不了关,心生一计,就冲向批斗台上,指着他的父亲的脑袋,挥动手臂带领大家高喊批斗口号,“打倒俺爹”,台下的群众也习惯的挥动手臂跟着喊,“打倒俺爹”,小伙子又喊,“把俺爹批倒批臭”,台下的人醒腔了,再没人跟着喊了。小伙子对村支书说:“书记,你可看到了,俺批了,他们不批,俺可管不了他们。”说完自己走下台,也过了关。
后来,外出上学,星期天回家还是喜欢到河边看一看,转一转,在河边静静地回想逝去的从前。后来参加了工作,回家少了,但经常梦见那条小河,脑海中像演电影一样闪动着过去的一幕一幕:苦难的日子,难忘的岁月,那清澈的河水,,伴我一起长大的杨柳,小伙伴们抹满清泥的脸,母亲在岸上喊我们回家吃饭的身影……小河成了我对老家的思念与眷恋,成了叩首铭记的乡愁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小河断流了——成了季节河,后来又干涸了,有人开始从河底挖沙子,人们开始填河建房子,几十户的人家把小河全占完了,没有了小河原来的一点痕迹。现在我回到老家,站在原来河岸的地方,朝着河的方向,看着满眼水泥建筑起来的高楼静静的发呆,我时常告诉我的孩子,这里曾经是一条河,一条美丽动人的河。
啊!小河,家乡的河,您永远流淌在我的心上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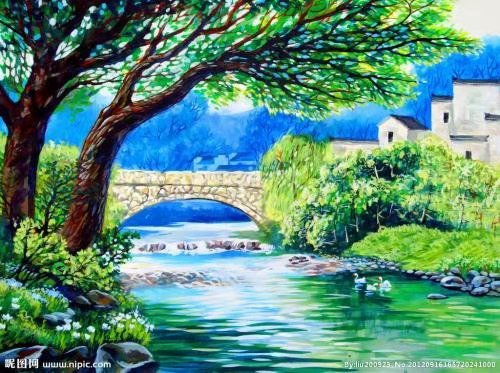
上一篇: 当手指爱上粉笔(张继革)
下一篇: 在努力中成长(王艳红)